當前時間為:
組織機構
魅力一中 輝煌卓著

一個數(shù)學家的榮辱觀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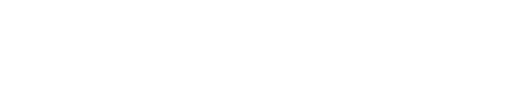
老校區(qū)
地址:新鄉(xiāng)市金穗大道51號
電話:0373-5082653
傳真:0373-5082653
郵編:453000
東校區(qū)
地址:新鄉(xiāng)市平原路東段
電話:0373-5056100
傳真:0373-5056100
郵編:453002
南校區(qū)
地址:新鄉(xiāng)市豐華路南段
電話:0373-3552588
傳真:0373-3552501
郵編:453000
掃一掃關注
一中官方微信

